內容提要:《孤城》由3个短篇组成,揭示了拆迁后富了的农民们的心态、生活。《岐路》说的是一对无知的青年夫妇,男的沉缅于赌博,女的由纯洁、善良到堕落,以致最后跳楼,悲惨地结束了年轻生命。《残阳》讲述了一位父亲的青年时代和晚年生活,一生大起大落,辉煌与苦难并存,最后被迫离开孤城。《富翁》则表现了一个农民的质朴、仁义、宽厚、善良的高贵品质。三篇小说皆耐人寻味,让人深思。
最近,孤城传出曲向东病了,而且病的很重,快要不行了的消息,还说支书、主任和一帮村干部去了他家,二十年没见面的女儿也回来了。于是,曲向东成了孤城当前议论的话题。
生病前的曲向东,一米七六的个头,长长的两腿,像倒悬起来的玉米棒子—样的黄白色的脸,有几分饱满,又有几分朴实。可曲向东说话两只眼睛老爱扑闪扑闪的,又给人以一种不成熟的滑稽狡黠的感觉。曲向东年轻时候就这模样,五十多岁了也没什么变化,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过的事多了,办事比较稳妥点。原来那没把门的嘴信口开河,胡喷乱碎,人们都叫他曲大喷。说话不着边沿,不切合实际。因此,在村里没什么威信,再就没个特长,就是没个什么手艺,只会种地。而种地也没技巧,生产队时候记工分,干活随大流,实行责任承包制后,就不行了,人家种些瓜果蔬菜能换钱,他还是老一式,麦子玉米,玉米麦子,尽管产量也不低,但是粮食卖上价钱,生活也就过得紧巴巴的,以至娶个媳妇女儿都两岁了,媳妇带着女儿不声不响地走了。开始,他四处找,去丈母娘家要人,头一两次,丈母娘还客气点,再去,丈母娘就翻脸了,说,你还问我要人,我还问你要人咧。你把我闺女用车拉您家了,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人没了,你不把我闺女找回来咱都不拉倒。最后一次,他听说老婆在丈母娘家里,他又去了。丈母娘在院子里端着畚箕捡粮食,丈哥拿一把锨准备给人家装土。他一进院子就说,妈,让我把娜娜和她妈接走吧。丈母娘说,她没在这儿让你往哪儿接?丈母娘看他一眼又低下头捡粮食了。他忍不住了,傻劲带出来了,腰一掐,有点盛气凌人的架势,说,我知她在家,你不让她跟我走,你是想给她再找个婆家再收一份彩礼是咋的?原来他们结婚时就因为彩礼闹过别扭,媳妇临上车时,要曲向东再拿八千块钱才让上车,把曲向东难为透了,他姐夫去借八千块钱才把人拉走。这是揭老底了。丈母娘一听气的放下畚箕找家伙就要打他。这边他丈哥骂了一声,你个龟孙,我让你在这儿胡说八道……。掂着铁锨就照他奔来。他一看势头不好,双手捂头拔腿就往外跑,边跑嘴里边吆喝,打人了,打人了,要打死人了。跑到大街上。这时村里不少人来看热闹,丈哥见他站着不走,嘴里还不停地乱喊,掂着铁锨撵过。他一看丈哥又撵来了,顺着大街往北一直跑到花马沟堤上,看看丈哥不撵了才站下。丈哥骂他几句转身走了,他手扶着一棵杨树,沉着脸看着离他远远的村庄,眼里的泪叭嗒叭嗒掉下来。时间正值初夏,娇阳下,小麦正在扬花,一股股南风吹来,一望无际的麦田像绿色的海洋,一起一伏地翻滚着波浪,空气里有花粉的甜香味也有干热风的呛人味。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了,最后揉揉眼,咽下—口唾沫,用袖子抹了一把脸,骂了句,好呀,你就死你娘家吧。转身大步回家了。打那以后再也没去过丈母娘家,也就从那时候起,媳妇和女儿再也没有回来过。
起初,他还想着,好,让你随便野,反正你没离婚,再结婚,你就是重婚罪。你野几年还得回来。然而,他没想到他媳妇到底没回来,多年以后,他听说她嫁人了,还为男方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他再也不想了,每日就是干活,打工挣钱。
曲向东也算是个正经人,不嫖不睹不吸烟不喝酒,可这些年到底没再娶上老婆。刚开始他还求媒人给他介绍,不断给这些人送礼,后来看看那些媒人吃了喝了并没给他办成,他觉得这些钱花冤枉了,谁再提给他找老婆的事他一概拒绝。自然也没人给他介绍对象了。他们村被折迁了,被拆迁的村民都成了百万富翁,那些大姑娘小寡妇、孤独的没伴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婆也都瞄向了孤城,想找个有房有钱的好小伙子好男人好老伴。于是,孤城里那些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汉都找到了伴,曲向东没有。不是没遇到,遇到了,而是这个女人和他过了几个月又走了。
这个女人才四十六岁,比曲向东小六七岁,人看上去也老实,长相也耐看,黑黑的圆脸,厚厚的嘴唇,一头粗厚的头发盘在脑后,只是那双骨轮轮的眼睛叫曲向东不放心。曲向东说,这女人的眼睛里有一种叫人琢磨不透的东西,她可不是过日子来的,她是为他手里的钱来的,虽然她有身份证,但她不是本地人,到时候把他的东西一卷走了,就是知道她是哪个庄哪个村的,你找不到人你有啥办法。他的前妻就是个例子。那时候东西金贵,家里做的一条新被子都拿走了,害得他一冬盖个薄被子冻得被窝都暖不热。过去,人们没有钱,铺盖衣服就是贵重东西。现在这些东西不主贵了,人都看重的是钱,他把钱一定要放好。这妇女倒是很勤快,屋里屋外都整理的井井有条,而且把身份证交给曲向东要他赶快办手续,领结婚证。这妇女越是催,曲向东心里越犯嘀咕,他心想,领了结婚证再离婚,财产就得有她的一半。不行,不能办手续。于是,他以为自己聪明,就给这女人说,办不办手续还不一样过。这妇女说,她男人死了,也没儿女。东西不会给谁,房产我也带不走。不管她怎么说,曲向东有个老主意,钱不能让她沾边,存折不让她知道在哪里放着,密码只能自己知道。他出来干活,每天就放家里点零花钱买菜,其他都不让这个女人管。这个女人原来的丈夫就是小里小气,干不成事,俩人常常生气,现在这个和死去的丈夫一个德性,对自己防贼一样防着,这样下去会生活好吗?于是,这女人就给曲向东丢下一句话,还是你自己过吧。背起挎包走了。
曲向东又过起了单身。也许他过惯了单身,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失。
三个月前,曲向东忽然感到身体乏力,厌食,右胸部有点隐隐约约地痛,也不想干活,就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肝癌后期,他感觉天像塌一样,—下子躺倒了。尽管他强迫自己该吃吃该喝喝,可吃不下喝不下,一见东西就想吐,没有办法。社区早上有早餐店,中午晚上有饭店菜馆,他到哪儿站站看看,就走了。不少人就说,你不吃不喝,要那些钱做啥,死了带不进坟墓里。他只是苦笑,有谁知道他心里的苦。
一天上午,曲向东从褥子底下拿出他放的存折,这存折一个是拆迁补偿款存折,一个养老保险存折、一个劳保存折、一个是平常打工工资存折,农信社的、邮政储蓄银行的、农业银行的、工商银行的,活期的、定期的,都有。还有一张欠条是侄子的,3万元。那一年侄子延青做农富产品生意,借给他三万,说好两分利息,最后赔了,现在连本钱也没有给他。他看看回忆回忆这些存折的来由,苦笑笑。忽然听到敲门声,他忙把本折放好,放在褥子底下,把褥子铺好去开门。这时候的曲向东已是骨瘦如柴了,个子没有缩小,只是肚子显得大,真是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了。
曲向东住进社区两年,在二楼,虽然住的楼层不高,却很少有人来串门。他侄子也只在借钱时来过,还有就是村医生小蔡近段时间给他看病打针常来,亲戚朋友几乎没来过。他以为又是村医小蔡来了。他打开门,一个姑娘站在他面前。姑娘有二十来岁,白色连衣裙,白色高跟鞋,高挑的身材,白瓜样的脸,脑后—束马尾辨,肩上挎一个白色小包,看着挺有气质。他怔了一下,好像在哪里见过,刚要问,姑娘甜甜把叫了一声:爸爸,我是娜娜。娜娜?曲向东的心里咚地跳了一下,很快反映过来,是女儿。前妻带走的女儿回来了。他又高兴又激动,上前拉住女儿的手,娜娜,坐,乖,爸给你倒水。
曲向东给女儿倒了水,娜娜坐下来。曲向东问起女儿这么多年的生活。娜娜说,小时候的事她不知道,是妈妈这两年告诉她的。她大学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有一个弟弟还在读大学。继父死了,是开大货车出事故死的。继父死后欠一屁股债,弟弟在上大二,连学费也交不起了,面临失学。妈妈想回来,问曲向东同意不同意。
曲向东当然不同意,那时候你不吭声离我而去,如今看我有房有钱了,要回来继承产业,搁给谁也不会同意。曲向东说,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妈不能回来。
娜娜问了问曲向东的病情就走了。她也不能埋怨父亲,是母亲有错在先。
娜娜走后不久,曲向东的病情加重了。每天要靠打止痛针维持生命。这一天,他让村医小蔡把支书、村主任、村民小组长,还有侄子延青叫来。在他弥留之际,他要把后事作个安排。尽管曲向东不是党员干部,但是,他病了,作为支书、村长,去看看孤寡老人也是他们的职责。
几名村干部来到曲向东家的时候,曲向东的侄子延青拿着药,女儿娜娜端着水正给曲向东喂药。曲向东有气无力地靠着被子半躺着,灰白的头发附在头皮上,像戴了顶破毡帽,颧骨突出,眼睛凹陷,倒悬着玉米棒子样的睑没有了血色。他看到支书、村长、村民小组长,要坐起来,支书毛卫民急忙拦住,别起来别起来,你躺着。这时曲向东的脸上现出笑意,有点不好意思地指指沙发,坐坐,你们坐。大概是村干部来看他有点激动吧,没有血色的脸泛起红润来。毛卫民说,向东叔,咋样,好点么?曲向东嘴唇牵动着下巴上的几根胡子说,不行了,不行了。村长老根打趣说,莫慌,阎王爷还没点到你的名字呢。曲向东苦笑笑,摇摇头,声音有点发颤,似乎有些悲哀:别宽你叔的心了,你叔知道,活不几天了。说着眼角里滚出两颗干涩的泪珠。他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睁开眼睛望着大家说,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事要和大家商量。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支书毛卫民是个三十多岁,很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方方的红脸堆满笑意,说,向东叔,有啥你尽管说,只要咱村咱社区能解决的一定解决,不能解决的向上级反映。
曲向东摇摇头,颤颤的手掀开身边的褥子,几个大红的存折、几张纸片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大家的目光也集中在曲向东的床上。曲向东先拿起一张折叠的纸,看看纸上的字叫道,延青,你过来。延青走到床前。曲向东说,这是你前年借我的三万块钱立的字据,说好给利息的。曲向东苦笑笑,你做生意也赔了,现在本息都不要了。也算叔帮你一把。延青也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开始他有些紧张,以为二叔要他还钱呢。当看到那张借条随着二叔的颤抖的手变成碎片,他的眼睛湿了,眼眶里有两颗泪滚动着想掉下来。他上前抱住曲向东叫了一声:二叔。曲向东应了一声,拍拍延青让他坐下。说,以后做生意看好行情,好好为人。延青点点头,嗯一声。接着,曲向东摸出一张农村信用社存折,叫女儿,娜娜。娜娜就在床边坐着,曲向东叹息一声说,这是这些年我打工挣的钱,十五万。你长这么大爹也没养你,你拿着这钱创业吧。娜娜接了存折,叫了一声,爸爸,已是热泪盈眶了。这时曲向东把几张纸片拢到几块儿,说,这是大张几个人借的,三百五百的,不要了。一下一下地又撕了。然后,拿起剩下的三个存折对着支书、村长、村民小组长说,这三个存折一个是农行的,一个是建行的,一个是工行的,一共七十八万。这是拆迁款,赔偿款。我这一辈子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共产党的政策好才让大家富了,吃水不忘打井人,你们把这钱转给学校吧。听说社区要盖教学楼。曲向东的话很稳重,声音很轻。
支书愣了,村长呆了,村民小组长张大了嘴巴。他们不敢相信平常软尔巴唧自私自利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曲向东做出这样的惊人举动,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啊。在场的人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了。曲向东把存折递过来,支书毛卫民犹豫了一下,庄重地伸出双手接过存折,激动地说,向东叔,我代表村两委,代表社区学校,谢谢你!
曲向东那苍白的玉米棒子的脸上现出微笑,好像他经过长途跋涉累了停下来休息,缓缓地闭上眼睛。
两天后,曲向东与世长辞了。社区的书记、主任,村党支部、村委会,全村的男女老少,社区小学的全体师生都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曲向东一定不曾想到人们会这么隆重地悼念他,要是知道如此,他该是一种什么心情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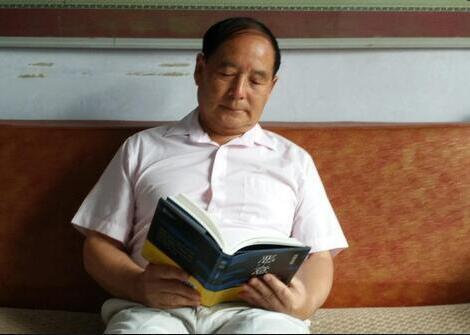
作者简介:罗辛卯,河南中牟县人,发表中篇小说19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200多篇,出版小说散文集《秋桃》、中篇小说集《天堂》《漩涡》《欲望》,其中中篇小说《蒲村》获郑州市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并被改编为电影剧本,《欲望》获郑州市第十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报告文学获河南日报三等奖,小小说《闪光的心灵》被收入《当代小小说作家代表作》。